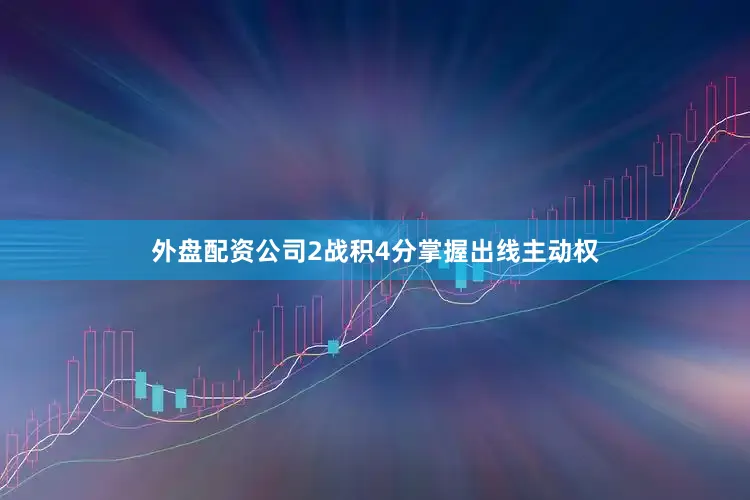如果人一定要有一个爱好……如果人一定要有一个爱好,何西阿推荐是猎鹿,这不是说钓鱼或者打牌,乃至抢火车抢银行这类的爱好不好,远远不是,它们都很好,但它们比不上猎鹿,猎鹿,人类征服自然最伟大的证明,山林间白尾鹿的短尾一闪而过,跳过溪涧,对着它们心脏来上一枪,欢欢喜喜把尸体抗上马背,然后获得好几天的食物。浪费?把尸体留在山林中喂狼和熊?浪费是可耻的,何西阿从不浪费自己的猎物,他满怀虔诚感谢地,感谢自然,感谢枪,去享用每头鹿,鹿腿烤了或者挂起来腌渍风干,鹿肉还可以做咸肉干,连内脏也有其用途,鹿皮那么美丽,毛皮无比丰盈,就算有蹭秃的一小片,也闪烁着皮毛主人生前的灵动,何西阿这时会说:“这只很调皮。”又可能整片毛皮有伤,他又说:“这次我瞄的不是很准。”
所以何西阿推荐猎鹿,即使偶尔,来到山林空手而归,那必然也是何西阿内心十分喜悦的时刻,他看着瞄准镜下灵动的身影,最后也没扣动扳机,因为今天既然被主祝福,那山林的野兽也该分享这份祝福,于是他最后看棕黄色身影消失在石头后面,放下枪,自得其乐地点着一根烟,即使这样,山间新鲜的空气、水珠和横陈在路上 折断的树枝也让人受益匪浅,何西阿喜欢这一切,当然他也可以拿一整天在山中猎熊、猎美洲狮、猎狼,追踪这些食肉怪物的脚印,不过那时心情可就紧张了,还是猎鹿,只要小心不被鹿角顶到,这些坏脾气又生动的生灵,有的长了一副可观的鹿角,不被鹿角顶到的话,整个猎鹿过程轻松惬意,最多不过是傍晚只拎着兔子回家,贝茜是不会嫌弃收获寒酸的,无论怎样的猎物她都能处理成美食,贝茜真好。
此外最好的猎鹿时间当属每年春天,冰雪刚化的时候,来到水边乌央乌央惊起一滩野鸭,每当这时候鹿就从林子深处钻出来觅食,不止是鹿,其他饿了一个冬天的动物都来到水边,然后猎人也来了,鹿的皮毛还像冬天那么厚实,在水里闪闪发光,何西阿的手开始发痒,要他说,什么是奇异恩典?每年初春的鹿就是奇异恩典,错过鹿的人要等一整年才能再见盛况,错过鹿的人根本就是暴殄天物,鉴于此,何西阿决定去猎鹿。今天就是好天气,今天就猎鹿。何西阿收拾了步枪,检查火药有没有受潮,把枪管擦了又擦,直到它看起来像一把能工作的好枪了,接着去跟亚瑟借铜币。
“嘿亚瑟,”亚瑟正倚在一棵树下打盹,好在今天不是他值守,小伙子是不是昨天晚上很晚才回营地?“亚瑟,醒醒。”可亚瑟脸上仍扣着那顶旧帽子,他翘着脚一动都不动,明显没醒。
“亚瑟,火车来了!”何西阿在亚瑟耳边大喊。
“火车?什么火车?来了。”亚瑟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旧帽子滚落在地,他脸上还带着刚睡醒的茫然,不过已经熟练地找起掩体,何西阿努力憋笑,想看他什么时候反应过来。
“……何西阿。”年轻人不忿地瞪自己导师一眼,“早上好。”
“早上好,亚瑟,我有个邀请函,邀请铜币先生跟我参加狐狸的欢迎宴会。”何西阿脱下帽子举手致意。
“铜币知道它是位先生吗?你都快把上流社会搬到营地来了。”
“My pleasure,my pleasure。”
“所以,这次是什么事?”亚瑟警惕地盯着何西阿,那双绿眼睛里永远有愤怒和活力,“像上次一样牵着狗出去骗人?赶牛的事它可干不来了,铜币就是……你知道就是铜币。”
“猎鹿,亲爱的男孩,这次只需要帮忙把鹿赶出来,轻松地就像抢劫醉汉,我保证。”
何西阿以为亚瑟又要抓着头嘟嘟囔囔转身捡帽子,跟以前没什么区别,接着大声喊铜币的名字,铜币会从任何匪夷所思的地方窜出来,闪电般扑进亚瑟怀里,有次他们甚至是在达奇的旧外套里找到小家伙,但是亚瑟抓了抓头发,这让他乱翘的金发更乱蓬蓬撇向各处,他浓密的眉毛蹩起来了,他说:“何西阿,什么是猎鹿?”
猎鹿,首先猎属于动词,是捕猎,打猎的意思,鹿,是一种偶蹄目哺乳动物,属鹿科,与古代欧洲贵族们打猎的马鹿不同,何西阿指的其实是广泛分布于北美大陆的白尾鹿。“哈哈,亚瑟,不要装傻,你懂得,猎鹿,从大自然手中讨点食物。”何西阿如此说道。
年轻人困惑地看着何西阿,显然没弄明白对方的意思:“我知道【hunt】,但什么是【deer】?是一种怪物吗?”他明显非常慌张,生怕对方再用他还有生词没学会为由,以拼写作业折磨自己。
“deer,deer is deer,”何西阿努力笑笑:“come on亚瑟,这个笑话很没水平,那种健壮地,四脚着地,头上长着角的动物,鹿!亚瑟。”
“哦你说叉角羚,”年轻人松了口气,“叉角羚什么时候改名叫【deer】了?这又是【玛修斯】式造词吗?”
“不是叉角羚,是鹿,角更大的那只,”何西阿比划着,“白尾鹿,记得去年经过阿拉法特潭在路上向你冲过来的那家伙吗?”然而年轻人仍然只是困惑地望着他:“我从没去过那,何西阿。”
“你在说什么?”
事已至此,何西阿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往常来说亚瑟没有这么固执,他是个不擅撒谎的人,更习惯用武力让人屈服,而且否认一头鹿的存在对他有任何好处吗?鹿那么鲜活,又健美,它的存在不会得罪任何人。
“你,”何西阿指着亚瑟,“你不知道鹿?”
“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何西阿。”小伙子大声抱怨起来,“我已经醒了,完完全全地清醒,用不着测试我。”
这不对啊?完全不对,鹿还在何西阿脑子里一跃而过,山涧非常非常宽,天又青翠地骇人,鹿从那上面越过去,像亚瑟的话从何西阿耳边越过,何西阿心想,好吧,他说:“好吧。”小伙子一定是睡昏头了,正好达奇叼着烟斗从旁边走过来,只要闻到那股烟丝味何西阿就知道是达奇过来了,明明新式卷烟更方便更干净,他还是习惯抽烟斗,当何西阿跟他提起他这种“少见的烟斗狂热”时,他说,你知道我,老派的作风,老派的性格,只有思想是新的,我们都在老世界里长大望着新世界,所以我想至少我还能保留一点旧时代爱好,而且烟斗劲大多了,你要不要试试?何西阿接过去试了一口,果然比卷烟味道重得多,但他下次还是选卷烟,可能这就是他和达奇不一样的地方,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意见一致,何西阿相信达奇肯定能明白鹿是什么。
“达奇,你在这,”何西阿叫住他,达奇正准备去河边看看,抱着书在那里消磨几个小时,“亚瑟忘了【deer】是什么,哈哈,多好的年轻男孩,年轻,还容易忘事,幸亏他还记得不要把警察带到营地里,(亚瑟在一旁抗议)你向他解释下什么是鹿,老朋友。”
但是达奇奇怪地盯着他,盯着这个老朋友,好像他说了很奇怪的事,比如有天他说我们应该金盆洗手,好好做个良民,再比如亚瑟说了什么傻里傻气的话,达奇说:“【deer】意味着什么新计划吗?或是任何事物的代称?”
“【deer】 is deer……”何西阿的声音停顿了,他意识到三分钟前他说过这话,面对着同样不解的眼神,然而达奇不愧是达奇,好像何西阿跟他玩了个新游戏一样,他立刻心照不宣的道:“我知道你老伙计,又是你那套新命名法,噢可别想瞒过我,”他举起双手,“你留着你的【deer】,我要去乘点炖肉,have a good day。”
达奇离开了,好像除了证明亚瑟是他教出来的——他们的想法几乎一样,之外,鹿还是不可避免的消失于众人之口。
如果人一定要有一个爱好……如果人一定要有一个爱好,猎叉角羚也不是不行,何西阿想,不过这很奇怪,突然鹿消失在所有人记忆里,不,也不一定是所有,我可以问其他人,也许亚瑟和老达奇跟我开玩笑,可何西阿不觉得他们的态度是开玩笑,他反而有点惧怕问其他人了,这就好比打开潘多拉魔盒,你怎么知道希望一定留在盒子里,而你怎能确定放出的又是什么灾难,派克显然不能问,他一直搞不清警察和军队的区别,对他来说那都是要击毙的目标,丹这小子不关心打猎,只有金子能让他提起兴趣,最近更是和一个妓女厮混得不错,夏安……上帝保佑夏安,达奇究竟从哪里找来这墨西哥人,他每时每刻都咳嗽那么厉害,简直让和何西阿担心下一秒他就把肺吐出来,他说自己家乡还有十五个子女,每月他们都跟雏鸟一样等着他们形容枯槁的父亲寄钱回去,不仅猎鹿跟他无缘,每次出门何西阿甚至担心他一头从马上栽下来然后他们不得不停下马,停在夜晚的野外把他原地埋了。
那就出去看看吧,我记得鸦喙那总有大把白尾鹿,像条白尾鹿河流,何西阿对自己说,对,出去看看,也许鹿躲藏起来了,藏到山洞里,藏到雪山上,藏进地心,藏得太久人们把它忘了。
何西阿抬起头,好在他本来就要出门,他手中还握着步枪,银元背上驮着他的毯子,所以他对亚瑟说:“我要走了,出门打猎,可能要去几天。”
“何西阿,你确定你没事吗?”亚瑟望着他,年轻人脸上的担心显而易见,可能何西阿坚持鹿存在的态度让他疑惑,疑惑而担心,他这么问到。
“我?我能有什么事,”何西阿举起手中的枪,“放心吧好先生,它会照顾我,银元也会照顾我,我简直活得像个国王、国王,亚瑟。”
“只要你确定……”亚瑟嘟囔着,默认了导师的离去。
穿过丛林,穿过草地,穿过两座对应的山峰,去猎鹿的地方,何西阿背对营地头也不回地跑开了,银元喷着响鼻甩开蹄子向前奔,风迎面扑在脸上,初春特有的寒冷夹杂着草腥气迎面而来,以往这时候,何西阿早早带上工具,告别了贝茜就往山下走,他们的家靠近一条河,每日他们从那里济水来梳洗浇地,以往这时候他早就钻进林子,在树木夹缝中看着那条河隐约出现又消失在树干后,白尾鹿的蹄印闪烁在每一棵红杉后,要很仔细才能追踪到这些狡猾的对手,多有意思,何西阿觉得自己现在就在那些最好的日子里——跟贝茜相伴的日子里,追踪着一头白尾鹿,所以银元才跑的这么急不是吗?要是追到了一头白尾鹿,就让贝茜炖鹿汤,用最好的鹿前腿肉,放上土豆和洋葱,不要吝啬地放上一大把胡椒。
贝茜坐在何西阿面前,她勾着一个桌布的花边,她总是这么手巧,是不是?鹿汤在炉子上热腾腾散发出食物的香味,何西阿能听到汤在汤锅里欢快地滚,他脚下踩着吱嘎作响的木地板,面前是有两道缝隙的桌子,其中一道是他偷偷玩快刀戳指缝戳出来的,被贝茜发现时女人拿手戳着他的头,教训他珍惜自己,要是你像酒馆那些醉汉那样戳伤自己,我绝饶不了你。贝茜恶狠狠地教训到。
“贝茜?”
“嗯?”
“贝茜汤好了,我去端来。”贝茜没有抬头,仍然在勾那些花边,白色丝线渐渐在她手下变成一片,何西阿眼睛有点花,他看不清上面每一根的细节,不过这不要紧,本来他也不懂花边,他也不懂生活,本来他只是个劫匪、骗子,小偷小摸的惯犯,后来贝茜来了,她谈着爱他,照顾他,手挨手眼对眼地教他,这才让他慢慢成为现在的何西阿。
“我去端来。”何西阿重复了一边,他转身去端那锅汤,清亮的一锅汤,汤汁浓稠得好似蜜糖,又干净,深褐色像鹿的眼睛,蔬菜和肉块从表面翻上来,热气滚滚,鲜香扑鼻,这是何西阿见过最好的炖汤,比他过去吃过的都要完美,他把汤锅端上桌,撤掉垫手的布料,拿来两只碗,一只同样有点开裂,木制东西在潮湿的林子里总会急着开裂,何西阿把有点开裂的那只放在自己面前。
“贝茜?”
“嗯?”
何西阿一边为贝茜舀了满满一碗炖汤,他把肉块和蔬菜块茎藏在汤面下,免得贝茜又为此大惊小怪前来检查他的炖汤碗,他把盛满了福乐——然而说到底它也只是一只炖汤碗,放在贝茜面前,轻声催促自己的爱人:“尝一尝炖汤,它曾经是最可爱的鹿,年轻又健康,就从我眼前溜走了。”
“我花了很久设陷阱,追踪它,终于还是让我捉住,这是这碗汤。”
“尝尝看,贝茜。”
贝茜还在低头不紧不慢地勾着花边,好像要从石器时代开始勾,勾到这一世代终结,何西阿禁不住有点着急,他催促道:“尝一尝。”贝茜仍然没有变,她仍然坐在光里,勾着那个花边,她现在比较像个印在画报上的影子,透过窗户的光线变了,汤凉了,但是她还坐在光里,何西阿渐渐看不清她的侧脸,那耸动的鼻尖,饱满的双颊,玫瑰色的唇消失了,灵活的双手被光晕吞噬了,渐渐何西阿连贝茜的轮廓都看不清晰。
“贝茜?”
这一次他没得到回答,何西阿悚然一惊,站起身想抓住妻子的双手,“贝茜?”然而他捞了个空,手的背后出现了一片山,一片山林,天空、草地,远处一个小点般的谷仓。何西阿从沉思中惊醒,他来到了鸦喙,银元驮着他走了很久,十分可靠地带主人来到目的地,可是鸦喙没有白尾鹿,任何属于鹿的痕迹都看不到,白尾鹿就如贝茜永远消失在光晕中,他回头,来处也是空茫茫一片,一瞬间这片旷野空旷的仿佛只剩下他一个人。
何西阿这才想起,贝茜不可能在这,距离贝茜过世已经过去三年了,他亲手埋葬……突然一种突如其来的无力洪流般汹涌而来,淹没了他,使他弯下腰去,把脸埋在掌心里,脸那么冰冷掌心却那么热,好像把一个人炽热的心丢进雪里,何西阿低声问自己:“鹿都到哪里去了?”
那是一八九二年,鹿终究闪闪发亮地逃走了。
益通网配资-专业实盘策略服务-合法的配资公司-上海股票配资招商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